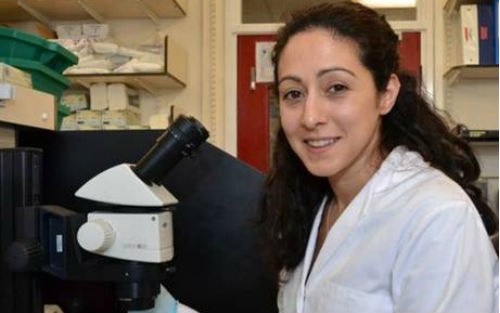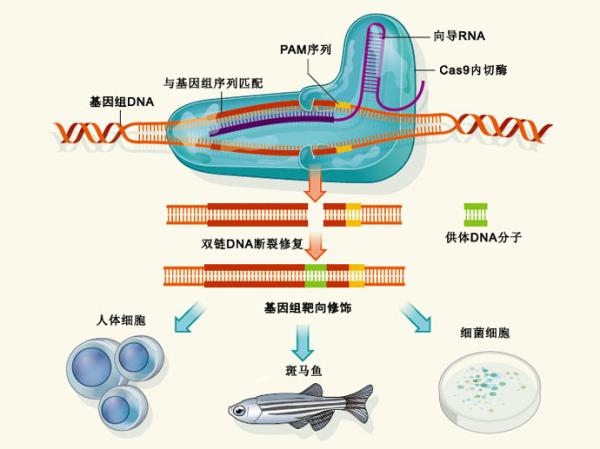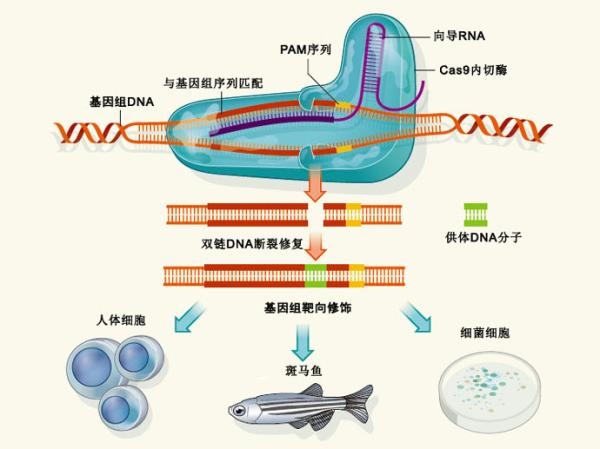作者 Daniel Brook
发表于《外交政策》九月/十月刊
哈佛医学院08届的毕业生具有非比寻常的野心,即使以哈佛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难得一见。他们之中,有一群不满足于“毕业于美国顶级医学院”的家伙,决定远赴海外为母校物色一个新的校友据点。当他们遍寻世界时,发现在这个被即时通讯和洲际旅行编织起来的世界上,在全球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区域的大背景下,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枢纽与全球门户,上海看起来注定将要成为新世纪中国际都市的翘楚。这里是梦想一夜暴富的淘金者的天堂,是一个全球瞩目的亚洲“黄金国”;而这一年的上海,已经将眼光放到了打造一个远东“巴黎”上——既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国际影响力上的。
不过,我说的这一年,是1909年。这批哈佛的医学博士花了超过三周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尽管如此,他们来到的这个都市,已经遍地是苏格兰来的鸦片贩子、犹太出身的地产大亨、锡克人充当的警员、祖籍广东的富商,还有那作为社交语言的蹩脚英语(被上海人戏称为“洋泾浜”)——上海俨然已是当时世上最开放的大都市了。在这里入关,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二十年代,一位客居上海的美国侨民对上海的世界化可谓不吝赞美之词:“今天若是一个旅客来到上海,他必将为眼前的事实所惊叹不已——高楼大厦;街道平整;旅店酒吧富丽堂皇,公园桥梁随处可见;马路上车流不息,巴士与电车往来穿梭;外贸商店数不胜数,入夜霓虹美不胜收——这一切与他在任何一个欧洲大城市所期待的、所习惯的没有任何区别”。
与此同时,这时的上海依然是个危险与机遇共存的地方。就在他们抵沪的几个月之后,上海所孕育的叛逆式的政治力量,将颠覆掉中国的皇权;而这些年轻医生们的投资,也将在几年之后付诸东流。
这个令他们心弛神往的国际化都市,诞生于数十年前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还是的西方强国首次迫使中国的皇帝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年代。在这个城市的范围之内,外籍人士丝毫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一样。治外法权,原本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罕见特例,却在这里成为了现实——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在上海那古老的城墙之外,一片一片的划分出了属于各自的租界,在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建起了一个人口达将近20万的枢纽区域。这个外来者始建于1845年的定居地,看起来就像是他们微缩版的故乡:法租界,因其绿树成排的街道和优雅时尚的咖啡屋而出名;英租界,以奢华至极的私人会所为人所知;美租界,商业街区的繁华兴旺无人可及。区区十年间,洋人统治下的上海已经取代了珠江沿岸的广东,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口岸;上海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只用了不过二十年的功夫而已。
但在这个生气蓬勃的都市里,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人却过着卑贱屈辱的日子。租界里的中国人干的通常都是体力活(洋泾浜把他们称作“coolies”,来自中文“苦力”的音译),因而常常被当做次等公民。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上海工部局甚至通过了一项种族隔离法案,在上海市内的大小公园内竖起了“禁止当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就连为西方顶尖企业工作的中国白领们,也一样只能使用中国人的专用厕所。尽管二十世纪初,中国精英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培育了自己的现代文明,为这个城市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活力,但国人身份卑微的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不堪其辱的中国人最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正是这个共产党,最终不仅将整个上海、也将整个中国对外封闭了起来。
时至今日,同样是这个1921年成立于在法租界的共产党,却正在引导着上海重新融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中国人领导下的上海,比西方统治下的那个上海更庞大、更完美,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更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局深知这个城市的历史之复杂,因而全力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也在打压着它在文化、学术与政治层面上的开放度——而正是这些因素,让百年前的上海既活力十足,却又难以驾驭。其实,当局对于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后果还是十分忌惮的——要知道,老上海的妄自尊大,曾经搞垮过一个老大帝国。
不过这早已是陈年旧事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对世界开放了一百个年头。如今情况大有不同:上海与国际的接轨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在上海前市长朱镕基的极力游说下,邓小平,这位在天安门事件中的外柔内刚的中共领导人,在1990年批准了上海的重新开发。在两年后对上海的视察中,他追加了自己的赌注,把上海称作是中国的“龙头城市”,据说他在通过一座连接了昔日的洋租界和新兴的市中心的大桥时,甚至还连连催促着“快一点,再快一点”。
几乎在一夜之间,上海,这座在1949年“解放”之后就几近停滞的都市,迅速恢复了在它共产党执政前的繁盛。九十年代,上海把毛泽东时期为废除私有制而没收的土地的使用权租给了房地产商们,从而筹集了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这笔巨款的支持下,上海当局迅速建成了世上首屈一指的民用设施,其中包括一座可以通过磁悬浮列车直达市区的崭新国际机场,一套规模超越了纽约和伦敦的地铁系统,还有一片片纵横交错的桥梁、隧道,把旧租界里的老城中心与对岸的浦东新区里的金融中心连在了一起。
在政府推动的发展大潮下,阻碍开发脚步的上海民居被强行拆除了。为了让上海重新成为国际贸易枢纽,上百万户家庭被拆迁安置。尽管这一重建过程曾一度被当作是个大包袱、甚至是开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倒车,重新开放的上海还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在房地产和金融界创造了可观的财富,重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其中也不乏汇丰、花旗这些百年前就曾在沪独领风骚的企业。九十年代末担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的言论尽管曾经饱受讥讽,但在如今看来却有了点预言的味道:“(我)故意超前地建设上海,就像精明的父母会给正在长大的孩子买件大一号的衣服一样”。上海惊人的发展速度确实令共产党的规划者们脸上增光,但它同样也带给了他们失控之虞。
浦东,这个邓小平曾催促着要“再快一点”的新区,如今已被林立的钢筋铁骨和玻璃幕墙所包围;这些现代建筑的闪耀夺目,让河对岸西方人在二十年代“装饰艺术”(注1)时期修建的外滩都显得相形见绌。摩天大楼无疑是这个在短短二十年间飞黄腾达的城市最光彩照人的写照;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一座,还装上了一整幅在夜色中闪耀的巨型LED幕墙。就像酒吧里的巨屏电视一样,无论播出的是什么,这座璀璨夺目的大厦都会牢牢的锁定众人的目光。一位来自欧洲的外籍建筑师把这些互不搭调的大厦,比作歌剧中的女服——引人注目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格调、甚至顺不顺眼都无足轻重。另一位美国建筑评论家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浦东追求的不是风格,而是规模——“浦东盖起楼来就跟嗑了药一样,那排高楼大厦完全抹去了河对岸外滩的优雅——就像是中国成片地对西方竖起了中指一样”。
除了城市本身结构的重建之外,上海在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实施上也尽力施为,力保重新与世界接轨的上海不会重蹈覆辙,陷入活力与屈辱交织的泥沼中而触发新一轮的革命。与当年那无需护照与签证的开放移民政策截然不同的是,如今的外国游客和侨民已经受到了当局严密的监控。洋人只占到了上海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待遇与当年的老上海那些无拘无束、精通外语的前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跟当今的国际枢纽更是大相径庭(就拿纽约来说,它的外国出生人口占到了37%)。当局并没有招引上百万海外专家来负责上海的全球贸易;它做出的选择是——汇集中国国内具有外语能力的职业人才。这其中的申请过程颇有精英大学的作风:内地人如果要获得上海的居留许可证,只需要从国内顶级大学毕业,并通过相应的计算机和英语能力的测试就可以了。
不过,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国人到上海谋生就要艰难许多。当局深知,当年成为共产主义者、推翻了1.0版上海的那些人,都是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因而政府采用了户口制度,来控制那些建造出新上海雄伟天际线的新生代苦力们。这一五十年代晚期诞生的制度,像专用于国内的护照一样,将中国公民和他的家乡绑定在一起。数百万中国农民涌入了建筑工地,在竣工之后又被遣返回了乡下。根据一份官方统计,上海一千九百万人口中大约六百万都是流动人口——而这一数字还被普遍认为是人为压低过的。农民工们经常无视暂住证的期限(具体数字倒从未被披露),因而检查身份证和清理外来务工人员之类的行动可谓司空见惯,尤其是类似在2010年世博会这样的重要国际活动之前更是接连不断。这样的歧视,在衣衫褴褛、肤色黝黑的外来务工人员和衣着入时、身体健康享有特权的市民之间,滋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矛盾(上海正式居民的人均期望寿命如今比美国还长,更别提他们的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多优秀了)。
如今的上海,同样也在迫使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以避免再次出现当年美孚石油和英美烟草在此榨取利润后输送回纽约和伦敦、让大量上海人一贫如洗的情形(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均寿命只有区区27岁而已)。1.0版的上海里,浦东曾作为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而臭名昭著;而到了2.0版的上海,那些扎眼的高楼,其实也还是一样建立在老上海的耻辱之上:那些血汗工厂只不过是转移到了长江上游更便宜的地皮上,由当地人掌控罢了。在强大起来的中国,洋人从曾经遭人痛恨的吸血鬼和蝗虫,摇身一变成了象征着上海国际地位的招牌告示。改头换面的治外法权——外国侨民比当地人享有更多的信仰和结社自由——也没有激起任何的民愤,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当局亦留意到,人们因为接触到了外国思想——那让人无限向往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外国来客而诞生了思潮,从而动摇了老上海的根基;因此,今天的上海政府对城市的学术和艺术生活严加掌控,其严密程度即使在监管甚多的中国内都属罕见。当年在洋租界的中国记者,躲开了皇帝的爪牙,创办了中国最自由的媒体。摸清了工部局共和思想的上海纳税人,甚至还在1905年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市议会,这可是在旧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代议制政府。不必多说,如今的政府无意在上海惹上媒体自由或是选举民主的麻烦。中国政府把这些人权轻描淡写地称为“全球价值观”,言下之意则是“与我们无关”——既不适用于中国,也不适用于它最引以为豪的国际都市。
即使是政治色彩不怎么鲜明的观点,只要是舶来品,也依然会受到监管和控制。三十年代的时候,联美、米高梅、华纳兄弟几大电影公司都曾在上海开设大型办事处;而现在,整个中国每年获准上映的外国电影也不过区区二十部。尽管1999年才启用的浦东国际机场如今已经拥有和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旗鼓相当的年客流量,但上海对外国文化开放的程度却依然还比不上“咆哮的二十年代”——当年上海的知名夜总会里,不乏来自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顶尖爵士乐大师的身影。而今天,自从比约克(注2)2008年在演唱她的歌曲“宣布独立”时高喊“西藏!西藏”以后,上海的市政当局就开始对来沪巡演的艺术家们严加审查了。2009年,新鲜出炉的上海艺穗节——类似于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年度艺穗节的翻版,同样是小成本大野心的现场演出舞台——被迫将它的国际演出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围的小城市;据主办方说,这是因为上海政府老爱给他们““生事”。即使中国的演员们也感觉上海的文化官员相当烦人:张守望,来着北京摇滚乐队“晕车的车”的领唱歌手,在赴美巡演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上海比北京管得严多了……有次演出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叫警察了。而且这在上海还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抑制各种自由表达的呼声,也算是政府为打造一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上海的努力之一。它的目的,是在进口各种国际商品的同时,不会捎带上那可怕的“全球价值观”。对远在北京那些古板的现代官员来说,2.0版的上海终极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闪闪发光的模范都市——口号可以是“全世界最快的火车”或者“比曼哈顿更多的摩天楼”——以证明这一自上而下的集权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一位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异常直率的解释,上海的复兴其实是共产党为了弥补毛泽东时代对这座城市的管理失当而做出的努力,以免敌对势力借此来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前总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写到,“解放前,上海曾是亚太地区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不止是香港,连新加坡和台湾都难望其项背。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已经被香港、新加波和台湾远远的甩到了身后。这让人不禁疑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到了哪里?”
今天的中国新政府,希望浦东新区的城市剪影,能够向人民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
(本文作者Daniel Brook,即将出版《未来城市史》一书)
———-
译者注:
1、装饰艺术(Art Deco),或称“装饰艺术风”,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源于欧洲的一种服务上层社会的艺术、建筑风格;
2、比约克(Björk),冰岛歌手,2008年3月2日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举行了演唱会,因其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而备受争议。
【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